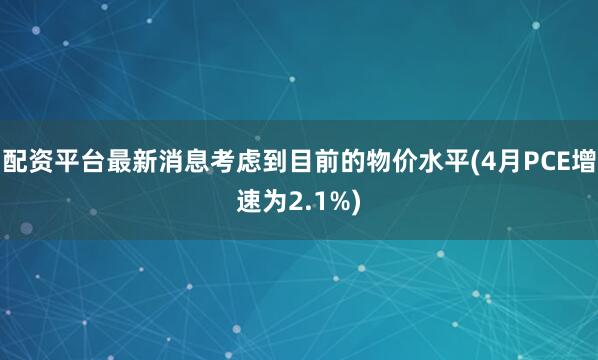从朱仙镇到后沟村
(摘自《天生我才:冯骥才传》,杜仲华著,中国言实出版社)
2002年新年伊始,河南朱仙镇,传说中岳飞大战朱仙镇的镇中心广场,万人空巷,一片欢腾,连墙头、屋顶上都站满老百姓。原来,这是河南省民协和朱仙镇政府合办的“全国年画节”开幕现场。
“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场面”,冯骥才对中国民协副主席白庚胜和秘书长向云驹说,“这个古老的年画之乡的人民,对自己的文化是多么热爱和自豪!这正是我们期待看到的!”
冯骥才致辞时,激动至极。寒流骤至,台上风大,他讲话时嘴巴冻得生疼,心里却涌动着一股热浪。
致辞后,冯骥才对白、向二人说:“咱们的抢救工程别等了,河南民协已经干起来了,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,反正我们已经立项了。”
“赞成。今天各省民协都来了,各大年画产地也来了,我们率先发动一下也未尝不可。”
“好啊,年画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一个龙头。再说春节不远了,春节是年画和年文化的活跃期,最利于做年画普查,错过春节就要错过一年。”
展开剩余83%于是,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干起来了。看似情绪化,实则很理性。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这次年画节时,用冯骥才开幕式上的一句话做为题目:《抢救民间文化,一天也不能等》。
下午,在中国木版年画研讨会上,冯骥才代表中国民协做了一个演讲,题目是“年画是民间艺术的龙头”。宣布要把朱仙镇年画节做为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龙头与开端。第二天,便邀集各地民协负责人召开“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工作会议”,具体布置了年画抢救与普查“为什么做,做什么和怎么做”。
冯骥才在山西榆次后沟村考察。
离开朱仙镇之前,冯骥才接到了山西省榆次县委书记的电话:“冯主席,我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山村,叫后沟村,小巧精致,遗存丰富,你有没有兴趣来这儿看看?”他打电话时,正坐着吉普车在后沟巡视,一口纯粹的晋中口音抑制不住内心的亢奋。冯骥才相信这位著名的晋商大院——王家大院的发现者和修复者的眼光,便满口答应下来:“好的,我们明天就从朱仙镇出发,前往后沟村!”
这是一次迷人的充满发现的山村调查。与冯骥才同行的除向云驹外,还有民俗学家乌丙安、民艺学家潘鲁生和乔晓光以及摄影师樊宇等。进入太行山东麓后,一座原生态的美丽如画的小山村赫然出现在眼前:它藏在巍峨而深邃的山窝里,下临清溪,上覆青林,在灿烂的阳光下,黄土其色如金,明亮耀目。一间间农舍依山而建,高低错落,聚散有致。令人惊异的是,山村里不仅有农舍,还有黄土高原上的各式窑洞;不仅有各类食品调料作坊,还有山神庙、关帝庙、观音堂等寺庙建筑。半山腰上,还有一个小广场,广场上有一座木构的戏台。村民们在山顶上种植果木与庄稼,足不出户,便可自给自足。徜徉其间,恍入“世外桃源”。
果然,经乌丙安现场考证,后沟村应为元代躲避战乱的“隐居村”。它虽离县城不远,但古人群山相隔,无路可通,将村落选在这样一个有山有水、风物相宜之地,确实眼光不浅。随后,一行人在观音堂的发现,给乌丙安的历史断代一个有力的佐证。在这个半荒废的寺庙里,他们看到了明代风格的彩绘画梁。一块明代天启六年的嵌墙碑《重修观音堂碑》上,镌有“年代替远,不知深浅”几字,表明早在明代天启年间,这座观音堂便是年代遥不可知的古庙了。
观音堂前,冯骥才发现两株古柏,灵机一动:庙中植树多与建庙同时,何不查验一下古柏的树龄?便托耿彦波请来榆次林业局专家提取木质,分析年轮,最后确定距今580年。按此推断,最迟元末此地已有居民。这就与乌丙安推测的后沟村建村时间不谋而合了。
冯骥才在山西榆次后沟村考察。
后沟村的独特景色迷住了摄影师樊宇。随冯骥才到后沟村采风之后,他又带领一个摄制组数度返回后沟村,记录那里的冬日风俗。为避免打扰村民,他们每次都自带睡袋,在寒冷的破庙里“安营扎寨”。大年三十子午交时,冯骥才忽然接到樊宇的电话:“冯老师,我正在后沟村拍摄,这里大雪封山,夜幕下,白皑皑的雪屋里闪着点点灯光,美极了!”
“哦,你们跑那儿过年去了!”
“是啊,您听,村里的人们正在燃放鞭炮!”
通过樊宇的话筒,他听到了“辟辟啪啪”的鞭炮声,清晰而响亮。里面还夹杂着他们的笑声。
忽然,鞭炮声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以为樊宇的手机没电了。
第二天一早才知道:昨夜樊宇高兴得忘乎所以,一脚踩空跌入雪窝里,险些墜入山谷!
莫非这些人都受了他的“传染”,对文化的感情竟如此纯真、执着、一往无前?
春节刚过,2月18日,中国民协在北京人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,冯骥才在会上发表题为《庄严的宣布》的致辞,阐述了一年来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考,宣布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——
冯骥才在考察古村落时发出的抢救呼吁。
“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从来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,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文化,一部分是民间文化。民间文化是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,数千年来积淀深厚,博大而灿烂,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。但是,由于历史的偏见,民间文化并未处在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,没有文字记载,不能登堂入室,大多只能凭借口传心授,以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。一旦失去传承人,就如断线风筝,即刻消失,化为乌有。因而,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一直是自生自灭的。这样,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今天,必然会遭受致命的冲击。
我们能让民间文化消失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吗?不能!
故此,我们决定要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、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,进行一次全面的、彻底的、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。
我们计划用十年,摸清家底,整理遗产,保护资源,光大精华。
这是一项纯粹奉献的工作。然而中国民间文化界已经背起这个沉重的文化十字架……”
致辞后离开讲台时,有记者问他:“冯主席,你今天为何如此激动?”
“刚才我在致辞时,感到内心不断涌出一种悲壮感,浑身上下火辣辣的。如果这时我去拥抱一块冰,一定会立刻将它融化。我不知自己为何胆子这么大,口袋空空,就敢声称要拯救全民族的民间文化。因为,这是我们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!”
发布于:天津市炒股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